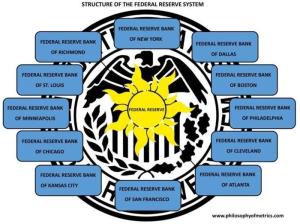当时龚忠武的反战同学在关心亚洲问题学者委员会学报(the Bulletin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)和“哈佛校报”(the Harvard Crimson)上,和费正清及他的助手沃格尔(Ezra F. Vogel)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论战。
1968年10月间,辩论的焦点,是质问费正清所主持的东亚研究中心,为什么要培训在当时反战学生深恶痛绝的中央情报局人员?他们认为,这根本违反了学术的自由和独立性,是可忍,孰不可忍?费正清被迫回应说,双方的合作是互利的,中心可以从“国防部”得到经费支持,并且可以从中央情报局获得机密资料!费的回答彻底暴露了美国“中国学”的真实面貌!原来所谓客观独立的学术研究祇是幌子,“中国学”骨子里祇不过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工具,是为美国的亚洲政策提供理论依据,如此而已!
龚忠武说,当他知道这些事实,他的思想陷入了严重的混乱状态;严重到失掉了论文的立场、大方向和前景,不知道应该朝什么方向来引导论文的论证。“这时我感到的是迷惘、失落、焦虑,陷于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,同我初到哈佛时的那种意气风发和乐观自信,适成鲜明的对比。我的哈佛之梦,开始幻灭了!”
孔恩说得很清楚,常态科学时期的所谓“检验”,并不是对理论本身进行检验。更确切地说,此种“检验”,受检验的是个别的科学家,而不是现行的理论。常态科学的目标在于解决谜题,而谜题之所以被认为是谜题,是科学家们接受了典范的缘故。所以解不开谜的罪过是由科学家来承担,而不在于理论。龚忠武在这样的冲击之下,陷入严重的思想和心理危机,“不知道论文究竟要写什么怎么写”,表示他已经没办法在“哈佛帮”的“典范”之下,从事“解决谜题”的活动,必须自行承担“解不开谜题的罪过”!
在那个年代,余英时选择的道路正好跟龚忠武相反。孔恩的理论“常态科学”让他瞭解:科学家的认识过程,基本上就是他在其所属之科学社群中的认识过程。科学社群中的学者,具有共同的训练与经验;他们是工作者,也是评价者;同时也是同行专业成就的裁决者。科学社群的成员必须通过典范的作用,才能看到同一个“世界”,并找到同一种问题解决方式。由于典范具有统一科学社群的定向作用,在常规科学阶段,它能保证整个科学社群都遵从同一个典范的指导。因此,在科学研究中,科学家对于问题的解答,是向科学社群里的同侪提出的,而不是向社会中任意的一群人提出的。
基于这样的认识,余英时在1970-1976年间,以〈反智论与中国政治传统〉一文为中心,建构出他的整套理论,这套理论巩固了“哈佛帮”的“典范”,也使他自己成为“哈佛帮”的一个重要成员。尽管1979年胡秋原已经以两万字的长文指出其论述的严重破绽,但在“哈佛帮”的权威笼罩下,对余院士“史学泰斗”、“思想史大师”的地位,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。 |